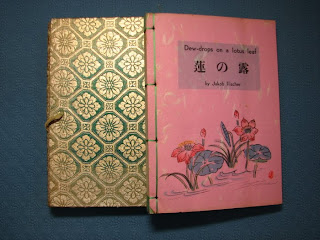陳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新序余英時
 《明報月刊》編者按:余英時先生研究陳寅恪先生的第一篇專稿《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刊登於香港《人生》雜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號。五九年香港友聯出版社翻印《論再生緣》油印本並收了《書後》作出版前言。不料,這驚動了中央領導人,郭沬若等親自披掛上陣。這是余英時研究陳先生著述遭遇的第一次風波。八十年代初,余先生在本刊陸續發表《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陳寅恪晚年心境新證》等文,其後本刊接到署名「馮衣北」的反駁文章並且刊登。「馮衣北」的反駁是在當時任中共中央局委員的胡喬木的指示下及廣東省委文教戰線負責人的布置下進行的。這是第二次風波。回顧兩次風波,余先生道──把眼光從官方移向民間,展望陳寅恪研究的將來,我是極其樂觀的。余先生還指出: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陳寅恪先生在大陸學術界越來越受到敬重。其中關鍵並不在他的專門絕學,而主要繫於他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兩句話並不只是說說而已,在最後二十年中他是以殉道的精神加以實踐的。
《明報月刊》編者按:余英時先生研究陳寅恪先生的第一篇專稿《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刊登於香港《人生》雜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號。五九年香港友聯出版社翻印《論再生緣》油印本並收了《書後》作出版前言。不料,這驚動了中央領導人,郭沬若等親自披掛上陣。這是余英時研究陳先生著述遭遇的第一次風波。八十年代初,余先生在本刊陸續發表《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陳寅恪晚年心境新證》等文,其後本刊接到署名「馮衣北」的反駁文章並且刊登。「馮衣北」的反駁是在當時任中共中央局委員的胡喬木的指示下及廣東省委文教戰線負責人的布置下進行的。這是第二次風波。回顧兩次風波,余先生道──把眼光從官方移向民間,展望陳寅恪研究的將來,我是極其樂觀的。余先生還指出: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陳寅恪先生在大陸學術界越來越受到敬重。其中關鍵並不在他的專門絕學,而主要繫於他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兩句話並不只是說說而已,在最後二十年中他是以殉道的精神加以實踐的。 今年(二0一0)是陳寅恪(一八九0─一九六九)先生誕生的一百二十周年,大陸上出版了不少涵有紀念性質的專書。最重要的是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三姊妹合寫的《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篔》(北京:三聯)、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北京:中華)和蔡鴻生《讀史求識錄》(廣州:廣東人民)。同時廣州《時代周報》也在八月九日出版了紀念專頁(李懷宇編)。可知陳先生逝世雖已四十一年,他不但仍然活在女兒和弟子們的心中,而且繼續受到新一代知識人的崇敬。
在這一特殊氛圍的感染之下,我也忍不住要對陳先生再度表示一點誠摯的敬意。自從《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增訂本出版以後(台北:東大,一九九八),我已退出了陳寅恪研究的領域。但是我對這一領域的關注卻沒有中止,十幾年來稍有關係的論著我大致都曾過目。現在藉着《釋證》重新排印的機會,我想就這些新論著中與《釋證》相關的部分,畧抒所見、所思、所感。
一九九七年十月,我為《釋證》增訂本寫了一篇《書成自述》,其中涉及大陸官方對我有關陳寅恪論述的一些反應。當時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出版不久,所引檔案資料相當豐富,然而在官方反應這一具體問題上,則尚欠完備。因此我的《書成自述》也只好概括言之,未能深入。現在新材料出現了,我覺得應該對這一問題重新回顧一番。
第一次風波
新材料中最重要的是關於我第一篇《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和《論再生緣》在香港正式出版,這兩件事自始便分不開,因為如果《論再生緣》不能與讀者共賞,那麼我的《書後》便不免陷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狀態了。關於印本《論再生緣》如何進入大陸以及官方的最初反應,我以前只看到下面兩條記載:第一、胡守為《陳寅恪傳畧》說:
一九五九年《論再生緣》的油印本流出香港後,被某出版商據以翻印,又在小冊子之前寫了一篇《關於出版的話》……香港《大公報》一位記者把這小冊子帶回廣州,交給陳寅恪,陳對這篇《出版的話》非常不滿,即把書送到中山大學黨委書記馮乃超處,並說明自己沒有送書到香港出版,當時馮乃超指出,《出版的話》無非想挑撥他同黨的關係,陳表示同意這一分析。(收在《文史哲學者治學談》,長沙:岳麓書社,一九八四,頁四一)
作者是陳先生在嶺南大學教過的學生,一九五九年恰好「受黨的委派」,以黨員的身份擔任了陳的「助手」(見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台北:聯經,一九九七,頁一八七)。所以《傳畧》所記的事實輪廓應該是可信的,至於陳先生是否對《出版的話》「十分不滿」,以及「同意」黨委書記的「分析」,則是另一問題,可以置之不論。第二,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
(一九五四年)二月,《論再生緣》初稿完成。自出資油印若干冊。後郭院長沫若撰文辨難,又作《校捕記》。(增訂本,上海古籍,一九九七,頁一五八)
郭沫若參加《再生緣》的論辯,我最早得之於《編年事輯》初版(一九八一),後來才在陸鍵東《最後二十年》中獲悉其全部經過(頁八九至九三),但這兩個事件之間有無關聯,則至今還不清楚。我曾有過一個推想,以為《論再生緣》傳至北京,也許另有途徑,未必是廣州中山大學呈報上去的。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陳垣給澳門汪宗衍的信說:
久不通消息,正懷念間,忽奉到《論再生緣》一冊,在遠不遺,至為感謝。惟書前缺去三、四頁,美中不足,倘能再賜我完整者一部,更感謝不盡。
同年十二月五日汪覆函云:
《論再生緣》二書乃寅老數年前之作,洗三家(按:洗玉清)屢為言之,乃其未成之稿,後流入港肆,被人盜印出售。偶得一冊,而書中間有累句,出版說明更推波助瀾,多違時之語,故特抽出三紙。頃承垂詢,檢出補寄,並另購一冊郵呈,祈查收。(均見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古籍,一九九0,頁五一一)
從這兩封信可知,一九五九年十一、十二月,陳垣各收到一冊《論再生緣》,又汪宗衍同年四月一日來函,賀陳垣「批准入黨」(同上,頁五一0),援菴老人新入黨,想必遵守黨紀,既知《論再生緣》在香港被「盜印」,斷無不向黨報告之理。因此我頗疑北京黨中央知有此事,或直接間接與陳垣有關。但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我也只能存疑而已。
驚動郭沫若等中央領導人
徐慶全《陳寅恪〈論再生緣〉出版風波》(見《南方周末》,二00八年八月二十八日D23版)是對此案發掘得最深入的文字,但因原文太長,不便徵引。下面我想通過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以下簡稱《年譜》)來處理這一公案。這部五十萬字的《年譜》是卞先生以九十九歲的老人,先後費去二十多年的功夫才完成的。全書對於相關史料的收集既廣,審查也嚴格。關於《論再生緣》一案,《年譜》不但充分運用了上面提到的徐慶全的專文,而且還參考了不少其他記載。以下我將順着《年譜》的時間次第,對此案始末先作一扼要的交代,然後再試加解說。
《年譜》一九五八年條末:
秋,余英時在哈佛大學偶然讀到《論〈再生緣〉》的油印稿本,後在香港《人生》雜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號發表《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一文,推斷《論〈再生緣〉》「實是寫『興亡遺恨』為主旨,個人感懷身世猶其次焉者矣!」(頁三0九)
又,一九五九年六月條:
余英時在美國哈佛大學發現的《論〈再生緣〉》油印本,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在海外轟傳一時,議論紛紜。書前加了一篇序言說像這樣的書籍,在大陸上是不能出版的。(頁三一一)
卞先生將我的《書後》和《論再生緣》的出版寫入《年譜》中,是因為這兩個互相關聯的事件很快便在譜主生命中激起波瀾,先後延續了三四年之久。
《年譜》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條:
楊榮國(英時按:時任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致函中華書局,云:「至於著作出版問題,中央同意,則貴局和陳進行商酌如何?」這裏所說的「著作出版問題」,只能是已經驚動齊燕銘、郭沫若、康生等中央領導人的《論〈再生緣〉》了。中華書局擬出版《論〈再生緣〉》,這實際上是對余英時以此做文章的回應,否則,我們很難解釋郭沫若會在一年之內排炮般地發表文章,因為如果是單純的學術研究的話,以郭沫若職務眾多、雜務纏身的情況看,恐怕是很難把精力集中於此的。與郭沫若有過交往的陳明遠,在談及此事時說,一九六一年郭沫若在研究《再生緣》之前,曾與康生交換過意見,隱約揭示出郭竟然對《論〈再生緣〉》產生興趣的深層背景(陳明遠《我與郭沫若、田漢的忘年交》)。如果陳明遠所言不虛,則郭沫若的研究實是負有使命。(頁三一四)
上面一段敘事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而且讀了之後仍然不免疑信參半。我的一篇《書後》和《論再生緣》在香港刊行何至於嚴重到必須「驚動……中央領導人」親自披掛上陣?關於這一點,下面我將提出個人的觀察,暫不多及。但上述的一切努力最後還是歸於泡影,《論再生緣》既未能在大陸出版,郭沫若「排炮般」的文章也無疾而終。
怕傷害中朝友誼周恩來叫停最後《年譜》一九六二年一月條(頁三二三),卞先生總結此案,分別徵引了三則史料:
香港出版《論〈再生緣〉》,一時轟動海外,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關方面與郭沫若、周揚、齊燕銘等人交換意見後,決定在內地出版先生著作與郭沫若校定的十七卷本《再生緣》,以回應海外議論。然而,由於這部乾隆年間虛構作品語涉「征東」,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特殊國際環境下,周恩來、康生出面中止對《再生緣》的討論,先生著作與郭沫若校訂本也被擱置起來。(徐慶全《陳寅恪〈論再生緣〉出版風波》,《南方周末》,二00年八月二十八日)
先生《論〈再生緣〉》出版一事,據當年中宣部幹部黎之回憶:「有一次周揚正在教育樓主持部分文藝領導人會議。康生突然進來,站着說:那個『孟麗君』(《再生緣》中的主人公)可不能再宣傳了,那裏面講打高麗,朝鮮方面有意見。他講完轉身走了。」(黎之《回憶與思考──從一月三日會議到六月批示》,《新文學史料》,一九九八年第三期)
年初,周恩來總理曾經讓人給郭沫若打招呼:「不要再在報紙上討論《再生緣》,以免由此傷害中朝友誼,在國際上造成不良影響。」郭沫若後來未再就此續寫文章,從此在報紙上停止了這場討論。(穆欣《郭沫若考證〈再生緣〉》,《世紀》,二00六年第五期)
綜合以上三種來源不同的史料,我們可以完全斷定,《論再生緣》事件確曾上達中共黨內最高決策層,所以最後必須由「周恩來、康生出面中止」。接着我要討論兩個相關的問題:一、郭沫若為什麼參加有關《再生緣》彈詞的討論?二、陳寅恪《論再生緣》為什麼最後還是不能在大陸出版?限於篇幅,我對於這兩個問題都只能點到為止,而不能展開論證。
先說第一個問題。《年譜》斷定郭沫若研究《再生緣》並非出於學術興趣,而是「負有使命」,這一斷案在所引種種史料中已得到充分的證實,可以無疑。問題在於郭的「使命」究竟屬於何種性質。我認為這是為《論再生緣》在大陸出版作開路的準備。郭研究《再生緣》涉及兩個方面:一是校訂出一部比較完善的《再生緣》版本;一是考證作者身世,與其陳寅恪《論再生緣》一較高下。他的第一篇長文《〈再生緣〉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陳端生》(《光明日報》,一九六一年五月四日),便顯露出這一雙重意圖。從《年譜》所引史料看,這是最初康生代表黨方和郭沬若、周揚等共同商定的策畧。黨的構想似乎是先出版《再生緣》校訂本和郭的考證,經報刊響應,先造成一個以郭沬若為中心的「《再生緣》熱」;然後在這一熱空氣中,將《論再生緣》推出。這樣一來,書中以含蓄文言所傳達的批判意涵便不致引人注意了。郭沬若的「使命」便在於落實這一構想。他在上舉第一篇長文中僅僅「不經意地提到陳寅恪《論再生緣》,而且用了挑剔辯駁的口吻」,以致引起有些讀者的不滿(見陸鍵東,前引書,頁九一)。其實這正是因為他一方面既布置《論再生緣》出版,另一方面又必須盡量減低它在讀者心中的份量。

其次,關於第二個問題,我也作一點補充。《年譜》揭出「朝鮮戰爭」的忌諱使郭校本《再生緣》印行一事胎死腹中,這大概是實錄。今本《論再生緣》結尾引作者詩句「青丘金鼓又振振」,自注云:「再生緣間敘朝鮮戰事。」(《寒柳堂集》,北京:三聯,二00九,頁八六)但一九五八年我所讀過的油印原本,這句注語則是「再生緣敘朝鮮戰爭。」(引在我的《書後》一文)。注語的更改是否出於陳先生之手,今不可知,但足證《年譜》記事確有根據。不過《年譜》中引康生的話──「朝鮮方面有意見」──似不盡可信,因為我們很難想像當時朝鮮方面有人讀過《再生緣》彈詞。「傷害中朝友誼」的顧慮大概來自中共內部。
陳寅恪不屑遷就出版要求
但陳先生《論再生緣》最後未能出版並不能完全歸咎於「朝鮮戰爭」的禁忌。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肯遷就出版者的任何修改或補充的要求。根據廣東省檔案館藏一九六一年《陳寅恪近況》,這年五月中華書局總經理金燦然曾拜訪過陳先生,提出請他將《論再生緣》一稿修改後,交中華書局刊行。「陳也有此意,但目前尚未着手修改」(見陸鍵東,前引書,頁三二八)。當時郭沫若正在考證陳端生身世方面與陳先生唱反調,並引出了新材料,所以他也有意對初稿有所補正,遲至一九六四年才寫成的《論再生緣校補記》,便是修改的成果。但最可注意的是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給陳先生的信,信上說:
我所編印之不定期刊《中華文史論叢》,在各方大力支持下,第一輯即可出版……。我們希望的是能得到先生的文章,以光篇幅。大作《〈再生緣〉考》雖未公開發表,但學術界早已遐邇傳說,均以未見印本為憾。據聞香港商人曾盜印牟利,實堪為恨。為滿足國內讀者渴望,此文實有早予公開發布必要。是否可交《論叢》發表,如何?甚望即加考慮,示覆為感。
此函寫在《再生緣》討論中止以後,可知黨方仍未放棄出版《論再生緣》的計劃,但方式卻有所修正。一年多前金燦然以中華總經理的身份親自登門請求,顯然是準備出一部專書,以示隆重看待之意(另有一九六二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也有刊行此書的計劃,不知可信否。見陸鍵東,前引書,頁三六五),而此時則改由該局上海編輯所出面,希望將此稿收入一個不定期的學術刊物,作為其中的一篇論文。這正是因為原始的構想流產,不得不大大降低出版規格,把它的流通空間壓縮到不能再小的限度。八月一日陳先生的覆信說:
又拙著《論〈再生緣〉》一文尚待修改,始可公開付印,目前實無暇及此。(以上兩信都出於高克勤《〈陳寅恪文集〉出版述畧》,《文匯報》二00七年六月三日八版,引於《年譜》,頁三二七)
他的答覆基本上和一年多前一樣,但他此時對書局出版他的著作,無論新舊,都不再抱任何不現實的期待了。為什麼呢?因為早在一九六一年或六二年初,他已將舊稿集成《金明館叢稿初編》送交中華,而遲遲沒有出版。《年譜》一九六二年「早春」條編者按語云:
慧按:蔣秉南(即天樞)見告:當時因先生原作有「黃巾米賊」語,出版方堅持更改,先生不同意其要求,直至先生沒世未得出版。(頁三二四)
蔣天樞一九六四年親至廣州拜壽,盤桓十餘日(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十日),此語必親聞之陳先生,絕對可信。又一九六二年五月間陳先生為《金明館叢稿初編》和《錢柳因緣詩釋證稿》(按:即《柳如是別傳》)兩書出版事,覆中華的上海編輯所云:
拙稿不顧意接受出版者之修改或補充意見。(見高克勤,前引文,引於《年譜》,頁三二五)
正可與蔣天樞轉述的話相印證。不但如此,陳先生最後在《論再生緣校補記後序》中說:
論再生緣一文乃頹齡戲筆,疏誤可笑。然傳播中外,議論紛紜。因而發見新材料,有為前所未知者,自應補正。茲輯為一編,附載簡末,亦可別行。至於原文,悉仍其舊,不復改易,蓋以存著作之初旨也。(《寒柳堂集》,頁一0六-一0七)

《校補記》痛駁郭沫若的考證,語多譏諷,讀者可自行參究。《後序》末數語堅持「不復改易」的原則,充分表現出他一貫的凜凜風骨。他至死未及見《論再生緣》在大陸印行,是出於他自己的價值選擇,並無遺憾可言。
第二次風波上面記述了我第一次寫有關陳先生的文字及大陸官方的反響。現在我要轉入第二次的風波,那已是陳先生身後的事了。關於第二次風波的實際內容,我在《釋證》全書中已有詳細的討論,這裏但補充一下官方的反響及其過程。
讓我徵述引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的敘述,先將事件的大輪廓呈現出來:
一九八三年,余英時在香港《明報月刊》的第一、第二期(《明報月刊》編按:即八三年一月和二月號)上推出他在一九八0年代的研究心得《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一年半後,余英時又一次在《明報月刊》上分別刊出《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陳寅恪晚年心境新證》等兩篇長文。並在同年七月的《中國時報》上刊載《陳寅恪的「欠砍頭」詩文發微》等文。一九八四年,余英時《文史互證、顯隱交融──談怎樣通解陳寅恪詩文中的「古典」和「今情」》一文,分別在十月份的台灣《聯合報》副刊上連載五天。
余英時近十萬字的文章可以稱得上是一輪排炮,在海外學術界引起相當反響。……一九八四年八月,署名「馮衣北」的辯駁文章《也談陳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與余英時先生商榷》在第二二四期的《明報月刊》刊出。如前文已述,「馮衣北」的反駁是在當時任中共中央局委員的胡喬木的指示下及廣東省委文教戰線負責人的布置下進行的。……一年後,「馮衣北」再撰《陳寅恪晚年心境再商榷》一文。兩個月後,余英時以《弦箭文章那日休》作答,發表在同年十月號的《明報月刊》上。(頁四九六─四九七)
以上引文中的敘事基本上是實錄,其中將幕後發號指示的人正式宣布出來,尤為重要。事實上,早在一九八三年年尾,我已知道胡喬木在積極布置向我進攻了。事有湊巧,當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有一位明清史專家來耶魯大學訪問,一見面便向我索閱《明報月刊》所刊長文。我很詫異,問他怎麼會知道我寫了此文?他說,在他訪美前,社科院長胡喬木曾有意讓他出面寫反駁我的文章,並說明:只有在他應允以後才能將那兩期的《明報月刊》交給他。他婉拒了這一任務,因此也失去了讀我原文的機會。很顯然的,胡喬木在北京一直未能覓得他所需要的寫手,最後才通過「廣東省委文教戰線負責人」找到一個「馮衣北」。關於「馮衣北」,陸鍵東先生告訴讀者:
在胡喬木的指示下,廣東省委有關方面開始布置寫論戰文章。此重任落在一九六0年代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系的一位寫手身上,反駁文章先後在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的香港《明報月刊》登出。(原注:署名「馮衣北」。)(頁三五九)
其實「馮衣北」的官方身份我也早在一九八四年便已一清二楚。這是因為《明報月刊》編輯部為了要我答辯,不得不以實情相告。編者信上說,「馮衣北」的兩篇《商榷》都是香港新華社轉交的,其中一篇文稿且在北京、廣州、香港之間周流了半年以上。所以我在答文中特別點名「馮衣北」是「中共官方某一部門」的代言人。最有趣的是「馮衣北」關於這一問題的回應。一九八六年「馮衣北」把他的兩篇《商榷》和我論陳先生的文字合成一「書」,算是他的「著作」,題為《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廣州:花城),其中大號字四十四頁是他的「正文」,而我的文字則以小號字排印,共一百六十七頁,作為「附錄」。儘管如此,我還是很感謝他;若不是託庇在他的兩篇《商榷》之下,大陸讀者是看不到我關於陳先生「晚年心境」的一系列文字的。「馮衣北」在此「書」的《跋》中說道:
區區一支禿筆,竟讓余先生產生「某個一部門」的錯覺,則筆者倒真有點「受寵若驚」了。
這是一個很巧滑的回答:上半句從我這一方面下筆,而有「錯覺」云云,但在他一方面卻無一字否認自己「官方代言人」的身份。下半句表面上好像是在回應我的「錯覺」,其實卻是暗中報幕後主人的知遇之感。只有如此理解,「受寵若驚」四個字才有着落。我的「錯覺」不但沒有半分恭維之意,而且適得其反,有何「寵」之可言?這裏我要特別感謝陸鍵東先生《最後二十年》對我的幫助。若不是他把胡喬木和寫手「馮衣北」的事調查得清清楚楚,並一一記錄了下來,我討論第二次風波的「官方反響」便會發生如何取信於讀者的困難了。
最後我想對《最後二十年》所涉及的一個重要問題提出一點不同的觀察。陸先生論這次風波說:
我們最關心的還不是這場論戰,而是胡喬木覺得有必要反駁余英時觀點的心態。陳寅恪不是一個家喻戶曉、具備新聞效應的熱門人物,理解陳寅恪的學術精神,遠非平民百姓樂意議論的話題。故此余英時的文章其實沒有太多的宣傳效應。促使胡喬木布置「反駁」,除了政治門爭的需要外,有一因素也許起着相當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二十餘年前,胡喬木與陳寅恪有過這麼一次談話。陳寅恪留給這位中央大員的印象,顯然有別於余英時所說的那樣。(頁三五九─三六0)
我過去也不很理解,為什麼官方學術界在陳寅恪問題上對我竟如此一再糾纏不已(見《釋證》一九八六版自序──《明明直照吾家路》)?不過我不相信,如上引《最後二十年》所說的,這是因為胡喬木對陳先生別有「印象」之故。
仍是「黨的決定」
現在關於第一次風波的事實已充分顯露出來了,我認為胡之所以全力布置對我進行「反駁」,主要仍是執行黨的決定。我為什麼能作此推斷呢?從前面有關《論再生緣》風波的討論,我們已看到官方那種如臨大敵的神情,以至康生、郭沫若都必須披掛上陣。此案在黨內留有檔案,決無可疑。我當年已是主犯,現在又變本加厲,大寫什麼陳寅恪「晚年心境」,則觸黨之怒,更不在話下。但老一代如郭沫若之流已逝世,胡喬木以社科院院長的身份正好取代了郭的位置。由他出面來布置「反駁」自然是十分適當的。以黨紀而言,他的布置不大可能是完全自作主張,而事先未曾取得(至少在形式上)組織的認可,不過具體的過程和可能涉及的人事現在還無從知道,只有等到檔案解密以後了。所以我認為第二次風波仍出於「黨的決定」,而且是第一次風浪的直接延續。
胡喬木曾間接表示善意胡喬木布置「反駁」的情緒表現得異常強烈,其中是不是含有某種個人的動機呢?我只能說,可能性是存在的,不過不是陸鍵東先生所猜的「印象」。我記憶中有一件小事可能與第二次的風波有關,姑妄言之,以備一說。一九七八年,我參加美國漢代研究代表團在中國大陸各地進行學術交流,前後整整一個月之久(十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七日)。接待我們的機構恰好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由副院長之一于光遠先生出面主持。在這一個月中,代表團受到了高規格的禮遇。由於擔任了團長的職位,我個人所得到的照顧更是特別周到(詳見我的《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何俊主編,李彤譯,台北:聯經,二00八)。此行我們並未見到院長胡喬木。但在離開北京前兩天,我有機會和俞平伯、錢鍾書兩先生談話,這件事我已經在《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一文中(收在我的《情懷中國》,劉紹銘主編,香港:天地,二0一0,頁一四七─一五四)。我們最初的討論集中在「曹學」、「紅學」的問題上,因為我在七十年代曾指出:幾十年來的所謂《紅樓夢》研究其實只是曹雪芹家世的研究。這個評論此時已傳到了北京,平伯先生便很同情我的看法。默存先生在討論中不經意地插了一句話,他說「喬木同志」也認為「曹學」之說在國內很少受注意,還要靠海外漢學家指出來。(原話當然無法復原了,但「喬木同志」四字則記得很清楚。)我當時只是聽聽而已,沒有接口。現在回想起來,這也許是胡喬木對我表示善意的一種間接方式,以中共官方接待外賓的慣例而言,他們對於來訪者的背景事先一定經過非常徹底的調查,然後才決定如何對待。我以往的一言一行,只要是有文獻可稽的,社科院有關部門大概都已弄得很清楚;我在《論再生緣》一案中的罪行當然更逃不過他們的注意。胡喬木當年雖未直接捲入第一次風波,然而他一九六二年春曾拜訪過陳寅恪,並為陳的著作出版作過努力,他對《論再生緣》案瞭如指掌,是可以斷言的。在這一背景下,他依然願意以善意相待,總算是很難得的。上面這段記憶是不是發生過如我所推測的作用,我完全不敢確定。無論如何,我在接受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招待之後,仍然寫出「晚年心境」這種「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文字,僅憑這一點,胡喬木非要對我窮追猛打不可,也是可以理解的。

官方學術界對於《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的正式反應,到一九八六年(即馮衣北《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出版之年)告一段落,但餘波似乎仍在蕩漾。大陸上出版我的著作已不在少數,甚至其中有些文字我以為可能通不過檢查的,最後居然都發表了出來。但唯有關於陳寅恪的研究,除了少數幾篇外,一律為政治編輯所否決,包括有些已「附錄」在馮衣北書中流傳多年的文章。這種情形並不限於一兩家出版社,而是各處皆然;也不是一時的事,而是自始至今無不如此。由於南北各大出版社政治編輯的口徑之驚人一致,使我不能不疑心黨中央機構或有指示下達全國所有出版單位,對我所寫有關陳寅恪的文字都必須從嚴審查。如果所測不誤,則我的檔案中的「黑材料」還在繼續發揮作用。
影響民間陳寅恪研究上面的討論都聚焦在官方反應的部分。只就這一方面着眼,則我的陳寅恪研究似乎從一開始便已被官方扼殺,在大陸上未能發生任何影響。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看,民間學人的反應則完全是另一種景觀。我關於陳先生的論述分別在一九八四、一九八六和一九九七年作過三度集結,每一次新版差不多都擴大篇幅至一倍左右。這三種版本雖都不能正式進入大陸,但是由私人攜帶入口的事畢竟防不勝防。我清楚地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中以後大陸外訪學人向我索書的,每月總有幾起;我請求出版家寄大批贈本來,先後也不計其數。另一條讀我的文字的途徑則是前面已提到的,即通過「馮衣北」書中的「附錄」。關於這一點,胡文輝先生在《陳寅恪詩箋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二00八)的《後記》中有很親切的記述:
回想起來,我在中山大學就讀,即一九八九年以前,恐怕還不知陳寅恪其人。對於寒柳堂詩的興趣,則是後來因馮衣北先生的《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而起的,準確地說,是由馮著所附余英時先生的論述而起的。(見下卷,頁九五六)
當時大陸學術界的朋友們也往往寫信給我,說他們從馮著得讀我的論文,恰可與胡先生的經驗相印證。最近研究陳先生詩集頗有心得的沈喜陽先生來信說:
先生《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喜陽所讀,亦購自書商複印本。(二0一0年七月二十日函)
我的《釋證》有大陸書商「複印本」,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
「陳寅恪熱」興起的文化心理
大體上說,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陳寅恪先生在大陸學術界越來越受到敬重。其中關鍵並不在他的專門絕學,而主要繫於他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兩句話並不只是說說而已,在最後二十年中他是以殉道的精神加以實踐的。在整個九十年代,大陸不少知識人為良知所驅使,不知不覺中對他「不降志,不辱身」以及「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的人格表現發生了很深的認同感。我相信這是當時所謂「陳寅恪熱」興起的文化心理背景。在這一氛圍下,我的《釋證》大概也更受到新一代讀者的注意,一九九五年陸鍵東先生的《最後二十年》便是顯證。這部書所發掘出來的事實和我的「晚年心境」極多息息相通之處,兩者幾乎可以說是互為表裏。
但是直接接着我的《釋證》而進行陳寅恪研究的,則屬於更年輕的一代,上面已提及的胡文輝先生即是其中成績最大的一位。他的《陳寅恪詩箋釋》詮釋了陳先生現存的全部詩作,包括聯語以至殘句。全書不下八十萬言,古典今情,各極其致。書中對我的說法質疑商榷者,不一而足。這一點最使我欣悅莫名,因為這是學術研究後來居上的唯一保證。他在書末寫了四首七絕,其第三首云:
義寧心史解人難,夜夜蟲魚興未闌。從世相知吾不讓(陳詩:「從世相知或有緣」),欲將新證補潛山(余英時原籍安徽潛山)。
末句是他的謙詞,我有自知之明,決不敢承當,他的朋友羅韜先生在《序一》中也說:
自潛山余英時氏以義寧解錢柳之法,還治其詩,拈出今典,鐵函乍廢,石破天驚。余氏之勝,在內證法,善以義寧之書證義寧之詩,辨其寄託,啓後來無盡門徑。此後解人繼起,眾訟紛紜,而文輝後出,加其邃密,得總其成。(頁二)
羅先生的獎飾之詞,我同樣受之有愧,但他推重胡文輝先生為解陳詩之集大成者,我則舉雙手贊成。胡先生解陳詩,一字都不放過,雖或有時而可商,然精解妙恪,觸處皆是;他最得意的「虛經腐史」,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詳見上卷「虛經腐史」條,頁三八四─三八八)。在這部《陳寅恪詩箋釋》完成之後,他仍然繼續不斷地搜求新史料以解決陳寅恪晚年生命史上的重要疑點。二00九年他根據《陳君葆日記全集》和《陳君葆書信集》,完全證實了陳先生在一九四九年曾有遷居香港的準備(見胡文輝《陳寅恪一九四九年去留問題及其他》,《東方早報‧上海書評》,二00年五月二十四日第八版)。無獨有偶,他的朋友張求會先生,另一位深研陳先生家世與傳記的學人,也在今年發表了《陳寅恪一九四九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證據》一文(見《南方周末‧副刊》,二0一0年四月二十九日,E28版),根據傅斯年致台灣省警務處的一份代電,證明陳先生這一年的五月曾有「自廣州攜眷來台工作」的計劃。胡、張兩先生都同樣聲明他們的考證是為了支持我在《釋證》中最後修訂的假設,這一點尤其使我不勝惶悚。我的《釋證》不過在陳寅恪研究的領域中扮演了一個「擁彗先驅」的角色,現在後起的健者早已遠遠地把我拋在後面了。但是他們仍不忘我這個早已脫隊的老兵,我終究是感到安慰的。
把眼光從官方移向民間,展望陳寅恪研究的將來,我是極其樂觀的。
二0一0年十二月十日於普林斯頓
《明報月刊》資料陳寅恪(1890-1969),江西省義寧(今九江修水縣)人,生於湖南長沙。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通曉二十餘種語文,史學脫胎於乾嘉考據之學。晚景淒涼,腿殘目瞽,死於文革迫害。
陳寅恪開創以詩證史、以史解詩的學術方法,很明顯是繼承了錢謙益「以詩證史」的方法,曾言「對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一生治學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已決定其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覆〉裏,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毛澤東)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於中山大學。此事於20世紀80年代方公之於世。
2001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陳寅恪集》,共十三種十四冊。
(原刊《明報月刊》二0一一年一月號,第四十六卷第一期,總五四一期)
 今年5月25日,是太平天國史研究一代宗師羅爾綱先生逝世十週年。最近我重讀了他的《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為他與胡適的師生情誼所深深感動。
今年5月25日,是太平天國史研究一代宗師羅爾綱先生逝世十週年。最近我重讀了他的《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為他與胡適的師生情誼所深深感動。